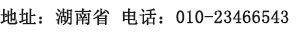静静的朱岩河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表弟伟平
文/墨雷
今日小雪。
“片片互玲珑,飞扬玉漏终。乍微全满地,渐密更无风。”无意中在拨出的电话屏幕上,看到视频彩铃中有玉树琼花的雪景,也有早先素未耳闻的唐代诗人无可的这首题为《小雪》的诗句在缓缓变换跃动,我才陡然意识到,天渐寒,冬渐深……
想起今天确乎在冷风中飘落过几片若有若无的雪花,转瞬即逝,大约也是上天为了满足人们对这个节气的期许吧。凛冽的风虽算不上刺骨,却也足够无情地撕咬下树上早已失却了绿色血脉却仍不肯挣脱母亲怀抱的余叶,任之飘零无依,随风盘旋,不知飘向何处……
静寂而漫长的夜已来临,街道上偶有车辆疾驰而过,也有三三两两包裹严实的行人在匆匆归泊,到处都给人以肃杀和冷清之感。只有居民区的灯光温暖如许,那是妈妈的怀抱,那是宁静的港湾。
这样的夜,适合思想,适合怀念,适合咀嚼和回味,适合写一些散或不散的文字……而我,则不经意想起了我的表弟伟平。这一切,皆源于刚刚母亲在电话里对我的叮嘱:等到了腊月初二,你拉着我跟你爸一起去烟台一趟吧,你伟平弟弟该烧三周啦……
于我而言,向来对日期数字不感冒,更何况一会阴历一会阳历,时常混为一谈,因而除却自己生日,别的日期总是浑然忘却。听了母言,立时呆若木鸡,内心深处滋生出无尽的怅惘和哀恸,氤氲蔓延开来,如枯败荒凉的衰草堆积,如如泣如诉的秋风吹过。
呜呼!不意姑姑唯一的儿子,我的表弟伟平过世将满三年啦?……数度忆及表弟,音容依旧鲜活,许久以来就想写文念想,竟迟迟没有动笔。许是万千思绪无从下笔吧,许是哀恸表弟英年早逝心有不忍吧,许是表弟生平零零碎碎并无耀眼之处吧……每念及此,便觉有千斤巨石压在胸口,无法释怀。
母亲的话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令我决定夤夜拾笔,赶在表弟三周年之前倾注笔端,一点一点撕扯掉堵在胸口的棉团,移去压在心头的块垒。
落笔之前,我先是拨通了姑姑的手机,转达了年过古稀的父母双亲意欲一同前往为表弟祭祀的意愿,不意姑姑竟是离奇的平静:“孩子,伟平过世已经快四年啦,去年烧过三周的……”我登时怔住了,甚至没有再跟姑姑寒暄,就扣了电话。
沉思间,表弟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正满含微笑地向我走来,用芝罘一带特有的口音唤我:“哥呀……”我顿时泪眼婆娑……
倘使表弟尚在人世,今年应该三十有九啦。换句话说,他在这个世界上仅仅生存过35个年头。在我的记忆里,表弟的音容永远地定格在少年时代:身材不高,胖乎乎极具肉感,慈眉善目,憨态可掬,像极了一个弥勒,一笑间,总会露出一颗小虎牙。
表弟生前跟姑姑一家居住在烟台市芝罘区黄务镇东珠岩村,一个距离烟台市里并不很远的村庄。村前,朱岩河不知疲倦地静静流过,不知这个村落是不是因此而得名。河面十分开阔,河流平缓,层层流波……
说起姑姑,从血缘上来说,其实跟我没有丝毫关联的。我的继爷爷跟姑姑的父亲是亲兄弟,但,我父亲自小随母从莱西老家改嫁至莱阳,而奶奶在我父亲年幼时就过世了,因此实际上,只是伦理间的亲人。但这并没有妨碍姑姑一家跟我父母之间往来亲密,远比有血缘的亲人为亲。
但在我印象中,姑姑远胜亲姑姑。她可是最有个性的女汉子,抽烟、喝酒、尖着嗓子骂人……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礼,姑姑已经学会了地道的芝罘当地口音,骂起人来拖腔拉调,不仅尖刻脆响,而且婉转高亢,在我听来,流畅而自然,像是花腔女高音,大有绕梁三日袅袅不绝之气派。当然,姑姑不仅嘴上功夫厉害,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甚至可以说比大老爷们还勤劳,还能干。
姑姑跟姑夫育有一女一子,女儿伟丽,儿子伟平自未出生就命运多舛。或许正如姑姑所说,表弟伟平原本不该来这世上走一遭吧?
听姑姑讲,早年怀表弟时,正赶上计划生育风声最紧的年代,姑姑打过专门不育的针,不意早已有孕在身,只是始终未曾察觉罢了。及至发觉,姑姑跟姑夫也是纠结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留下这条来之不易的小生命。这在当时,可是法不容情的。万般无奈,姑姑开启了逃亡生涯,偷偷回老家避难。不意,神通广大的“小分队”还是闻风而至,风声鹤唳的姑姑听到敲门声后,毅然决然地从窗户跳出,才逃出了生天。几经周折,表弟伟平还是平平安安降临。这自然给一家人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快乐和欢喜,至于处罚点银两,就无足轻重了。
美丽富饶的东珠岩村前有开阔的朱岩河缓缓流过,后有青山环绕,景色宜人,这也成就了姑姑姑夫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质朴能干。自我打小姑姑就对我无法言表的亲昵,甚至丝毫不亚于我的爷爷和姥姥。尽管相距有近华里,但我从小到大,在姑姑家住过的时间委实不少。姑姑也总是带着我一同上山,一同下河,却从来不让我劳作。她上山砍柴时,就给我讲村里的风土人情,砍满一车鲜活的松枝推回家来,也不经晾晒,直接拿来烧火做饭。她也跟姑夫偷偷到朱岩河边挖河沙,那么大的车,他俩顶着炎炎烈日,一锨一锨装得满满的直到冒了尖,再拉出去卖。我觉得太阳快要将我烤熟一般,幸好旁边有清清的朱岩河在缓缓流淌,波光粼粼,给我带来丝丝凉意。而姑姑和姑夫也累得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但他们很有成就感,日子因此过得极为殷实。我知道,那其实都是用血汗换来的。姑姑抽很重的烟,大多是老家爸爸等亲友送的老旱烟。也跟姑夫一起喝浓烈的酒,我印象中喝得最多的,就是那种简装的烟台白干。
从小到大,“到烟台姑姑家”就成了我的向往和期盼,时至今日,若是到烟台,只要得闲,一定要到姑姑家看望,方便了,就陪姑姑姑夫喝一杯。近几年,姑姑喜欢上了制作辣椒酱和拉花萝卜,尽管制作程序很繁琐,花费颇巨,但姑姑总是乐此不疲。同村人因此而大饱口福,而姑姑从不会收取一分钱。每年莱阳梨成熟的季节,我就会驱车前去看望姑姑姑夫,顺便捎几箱莱阳梨。而姑姑则总是让我拉回满满两大桶她制作的辣椒酱和香脆可口的拉花萝卜,经过她的加工制作,这些食品都经年不坏。
当年我还不满7岁时,就跟姑姑一起乘车到烟台市里,在她父亲的工厂住过一晚。依稀记得跟姑姑在一张单人弹簧床上睡过一夜,我俩各在一头,不知道睡相不老实的我有没有蹬到姑姑?
后来,我长到11岁,父母让我独行到姑姑家小住。我被生意人用货车载着到车站,自己乘坐绿皮火车,到姑姑村庄附近的车站下了车,顺利抵达。姑姑一家跟父母都对我赞不绝口。
那时表妹表弟尚年幼,但,对我都十分有礼。尤其是表弟伟平,总是笑呵呵的,围着我哥长哥短。许是继承了姑姑姑夫的热情好客的天性吧,我每次来,都拉着我的手回家,还学着姑姑的腔调:“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啊?”我就笑了。因为父母每次都会嘱咐我,你姑姑姑夫就喝烟台白干,你到村头的商店拿两提就好啦。以至于商店的女主人一见到我,就会热情地说:“又来走亲戚啦?还买酒么……”
表弟跟我玩得总是不亦乐乎,跟他亲舅也就是我伯父的儿子虽然同村,却如针尖对麦芒。他俩同岁,一个胖,一个瘦。玩恼了,叔兄弟就喊表弟“胖猪”,表弟也不甘示弱,就一个劲回敬叔兄弟“娄金狗”,我听了他俩的对骂总是忍俊不禁。
天有不测风云。天真烂漫的表弟长到九岁的时候,忽然头部出现了疾病,姑姑姑夫抱着他到村里看了医生,说是得了脑炎。那时交通尚不发达,姑夫骑了大金鹿医院。后来,诊断出,表弟脑中是长有瘤子的!这个消息不啻于惊天霹雳,姑姑姑夫哭着跪着央求大夫,无论如何都要帮忙医治。由于脑瘤长的位置极为险要,直接手术的话,成功的把握实在是微乎其微。保守的方案是在头顶打开脑颅,将瘤液通过体内消除。那时的医疗条件尚不发达,许是姑姑姑夫的诚心感动了上苍,抑或是表弟的淳朴善良福佑他命大,同病房的病患不日后大多离世了,只有他奇迹般的生存下来。医生还是告诫姑姑,尽管手术成功,但,后遗症是难免的,也未必能有多久寿命。可以想见,姑姑姑夫有多伤心欲绝。
当年在寒暑假期间,我要到烟台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鲁东大学面授学习三年,我一直居住在姑姑家里。然后,骑上自行车到学校学习,省却了不少住宿费和餐费。姑姑家里有五间房,让表弟把房间倒给我,他跟姑姑姑夫一起睡。表弟从没什么怨言,从来不抱怨,总是乐呵呵的,仿佛弥勒佛一般。使我总会想起那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对联。
姑姑不仅勤劳能干,还十分洁净,再忙再累,也总是把家里擦拭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家里的水泥地面每天都要拖三遍,雷打不动。只把拖地的活交给表弟来做,偶有不顺意,姑姑也会大声呵斥几句:“你个不中用的,成天就知道吃,就是个造大粪的机器!”表弟从不辩解,从不生气。我知道,姑姑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表弟哪里不舒服了,最上心的也是他。
她还喜欢变着花样做着吃,一家人也都养活得白白胖胖,一家人体都达到了次重量级。整天在姑姑家里吃住,我心里也不落忍,想给他们再买点什么,总是被姑姑呵斥回去。表弟也十分懂事,我给他买的什么东西,他都给我揣到口袋里,说什么也不要。记得那一次,我在市场上割了一块生猪肉,放在包里,又买了点青菜。回家后,姑姑看到我买的菜,张口就一顿训斥,弄得我再不敢拿出包里的生肉。过了两天,担心坏掉,找到伯母,偷偷给了她才完事。但姑姑对我总是十分慷慨,拿我当个孩子,我每次要返程时,都送给我红包。我自然坚辞不受,表弟就会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地忘我口袋里装:“哥呀,给你你就拿着吧……”我竟不忍再推辞。
那时候,姑姑村里猫狗极为常见,至今,她家里还养着三四条宠物狗。那几年,我们村里草狗并不多,不少都因误食耗子药殒命。姑姑就一次次把养好的狗狗装在纸箱里,让我带回老家看门。我知道,表弟跟狗狗极有感情,换做我,一定会不舍得送人,但他都从未有异样的反应。记得有一条非常可爱的半大黄褐色的狗狗,姑姑给它起名换做“吠吠”,我带回家之后,全家都十分喜爱,吠吠很通人性,非常温顺,看起门来却十分尽职尽责。我大婚期间,姑姑一家前来道贺,表弟搂着吠吠爱抚了许久,还合了一张影……
尽管表弟伟平的智力水平、身体发育深受脑部影响,但总算顺利地成长起来。只是在20岁那年,脑瘤又发作了一次,大约是脑里的积水压迫造成的,幸亏多方医治,表弟的生命才得以延续下来。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同龄人都渐次成家立业,而表弟伟平依旧像个长不大的男孩。大家都对他无欲无求,但求他能健康平安。可惜的是,人有旦夕祸福,天不遂人愿。四年前,表弟的脑瘤再次发作,医院医治。先进的仪器测知,脑瘤造成了血栓,已经无法医治!姑姑姑夫再次伤心欲绝,看着重症监护室里的儿子,欲哭无泪。我跟父母闻讯赶来,医院里人满为患,尽心宽慰了他们一番。姑姑姑夫夸赞说,幸亏表妹能够独当一面,肩负起照顾弟弟的重任,他们的哀痛才减缓了不少。我跟父亲拿出红包给姑夫,一向要强的姑姑看到后,流着泪谢绝。我更为哀伤,便不再客套,直接扔下红包就跟父亲离去。
后来,我在电话里问询过几次,姑姑总说,情况一直不乐观,多亏了表妹抛下了所有事物,悉心照顾弟弟。我安慰了姑姑一番,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祈盼有奇迹发生。
几个月后,表弟回家静养了一段时间。之后,表妹把医院康复。医院探视,看到表弟的头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带着呼吸机,已经无法言语。表妹正在忙着给他擦拭身子,跟我们打完招呼,就说要带着表弟下去做康复运动。我们当即一同前往,表妹不需要我们帮忙,十分熟练地将表弟抱到轮椅上,推着他跟我们一起乘坐电梯来到地下康复场所。表妹把弟弟抱下来,放在特制的床板上,紧紧固定好,然后,操控床板旋转,让表弟得以活动那些麻木的部位,期望能够恢复日渐麻木的知觉……借助床板的力量,表弟算是“站”了起来。父亲看到表弟眼皮抬了一下,嘴巴动了动,脱口喊道:“伟平,你还认识我吗?”
表弟直视着我们,说不出话来,却用力地摆了摆手,我知道,那是在跟我们打招呼!说明他认出了我们……我的眼泪“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来不及擦拭,拿出手机,留下了这个神奇的瞬间……而这个镜头,就这样永久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多少年过去了,一直挥之不去,一直鲜活而清晰……
从医院出来,我们到姑姑家里小坐了片刻。姑姑流着泪说,很想跟了伟平去,又丢不下表妹……父亲安慰着姑姑,而我,则感同身受,深深懂得姑姑的那种悲伤。都说,儿是娘的心头肉啊!我心情难以名状的沉重,又悄悄在炕席下放下一个红包,然后,驱车跟父亲离开了……
没成想,那竟是我跟表弟的最后一面。不久之后,表弟还是安详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短暂的人生,没有来得及谢幕,就永远地画上了休止符。我从没见他喊过痛,也从没见他流过泪,更没听到他要留给亲人的语言,而我,却会时常为他哀恸流泪。
不记得哪位诗人曾写道:“但不幸的是
我已经不需要再依靠美好的事物
活下去
认识到自己只是蝼蚁
认识到更多人只是蝼蚁
就不再悲痛。”表弟孙伟平无疑是极为平凡极为渺小的,渺小的如草芥,如流星,如尘埃。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这天地间最卑微的存在?表弟什么都没有留下,或许多年之后,将被浑然忘却,再也无人提及。
正如这静静流淌着的朱岩河水,我们无从知道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偶尔也会翻卷起微小的浪花,或者因风荡起层层涟漪,然后很快又趋于平静,继续奔流不息。
天空没有痕迹鸟儿却已飞过……作者简介:
董成伟,笔名口天,网名剑胆琴心,男,山东莱阳人。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多年,中学高级教师。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莱阳创作之家副秘书长。自幼酷爱读书写作,先后在《山东教育》《作文教学通讯》《烟台教育》《当代散文》《齐鲁晚报》《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胶东散文》《今日莱阳》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散文《母亲节感怀》先后在《山东教育》《当代散文》发表,入选《胶东作家亲情散文选》,并获“黄海数字出版社《胶东散文年选()》优秀作品奖”,获胶东散文年选()最佳作品奖。年被评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优秀会员。作品入选《胶东散文十二家·董成伟卷》《美文十二家》。
黄海散文双年刊第篇文章
顾问:毕淑敏、邓刚、丁建元、王海峰、许晨、王安、刘长胜
总编:焦红军
副总编:马学民、刘玉涛
执行主编:王雪娟、彭丽洁、梁绩科
投稿邮箱:huanghaisanwen
.